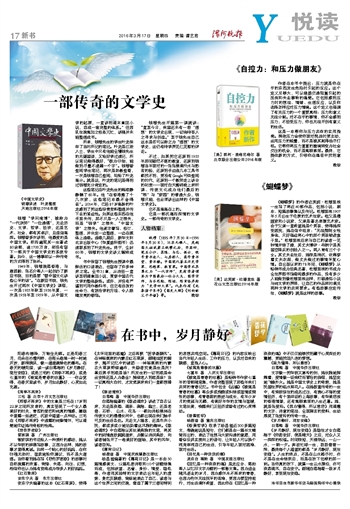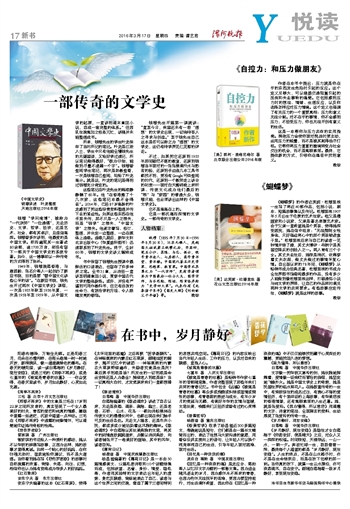钱穆“学问淹博”,被称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却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
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
所幸,钱穆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自己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
这些笔记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他“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连载几期后,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迅速联系到了叶龙先生。终于,尘封60年,钱穆的文学史讲义辗转成书。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钱穆先生开篇第一课就讲:“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至于钱先生自己这本是否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文学史,这仍有待学界见仁见智的评论。
不过,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通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一部传奇的文学史。
人物档案: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刘向歆父子年谱》等。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