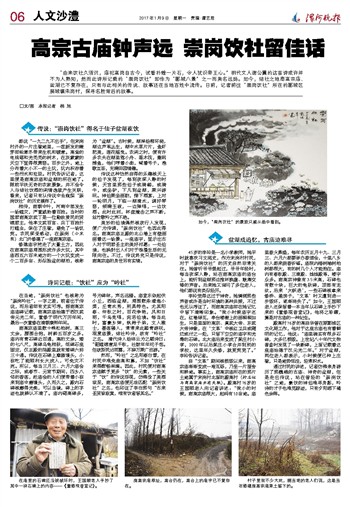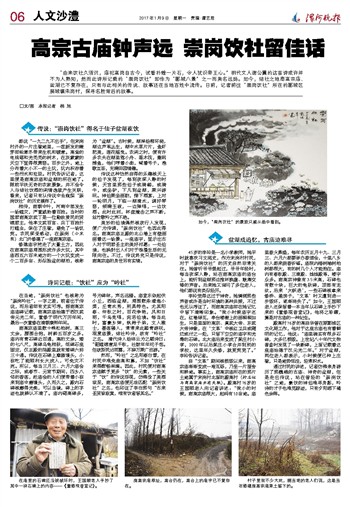“由来饮社久消沉,庙祀高岗自古今,试看扑蝗一片石,令人犹识帝王心。”明代文人谢公翼的这首诗或许并不为人熟知,然而此诗所记载的“崇岗饮社”却作为“郾城八景”之一而美名远扬。如今,结社之地商高宗庙、盆湖已不复存在,只有与此相关的传说、故事还在当地百姓中流传。日前,记者前往“崇岗饮社”所在的郾城区裴城镇宋岗村,探寻名胜背后的故事。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传说:“崇岗饮社”得名于仙子盆湖夜饮
都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但宋岗村外的一片庄稼地里,一茬新发的嫩芽却给寒冬带来生机和暖意。高耸的电线塔和光秃秃的树木,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很萧瑟。百步之外,地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土坑,坑内积存着一些污水和垃圾。村民告诉记者,这里便是商高宗庙和盆湖的所在地了。眼前平淡无奇的农家景象,并不会令人与结社饮酒的闲情逸致产生关联,看来,记者只有从传说中去窥探“崇岗饮社”的历史模样了。
相传,商朝中叶,河南中部发生一场蝗灾,严重威胁着百姓。当时的国君商高宗武丁是一位勤政爱民的贤德君主,他率文武百官、兵丁百姓扑打蝗虫,保住了庄稼,避免了一场饥荒。农民深受感动,在崇岗(今宋岗)北门外修建了一座商高宗庙。
修建庙宇挖走了大量土方,因此在商高宗庙周围形成许多大坑,其中庙西五六百米地方的一个大坑变成一个二百多亩、形似脸盆的湖泊,被称为“盆湖”。古时候,湖岸杨柳环绕,湖边芦苇丛生,湖中水草片片,鱼虾肥美,莲花摇曳。农闲之时,便有许多农夫在湖里驾小舟、荡木筏,撒网捕鱼,他们哼着小曲,喊着号子,渔歌互答,充满田园情趣。
传说这种怡然自得的乐趣被天上的仙子发现了,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天宫里那些仙子或骑鹤,或骑牛,或坐驴,下凡到盆湖,乘兴游玩。神仙乘坐画舫,摆下酒宴,上对一轮明月,下临一湖清水,调好琴瑟,倾满玉液,一边弹唱,一边饮酒。此时此刻,杯盘撞击之声不断,丝竹歌吟之声不绝。
美妙的仙境偶然被夜行人发现,便广为传诵,“崇岗饮社”也因此得名。商高宗庙正殿的北山墙上有壁画画着这一场景。一座庙宇,显示出古人对于明君圣主的美好祁愿;一处仙境,也映射出人们对于浪漫生活的无限向往。不过,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商高宗庙的身世另有实情。
诗词记载:“饮社”应为“吟社”
在当地,“崇岗饮社”也被称为“崇岗吟社”,一字之差,前者出于传说,而后者却有史实可考。据商高宗庙庙碑记载,商高宗庙始建于西汉武帝元光二年,重修于明代万历年间,最后一次重修在清朝康熙年间。
商高宗庙里数十株松柏树,高三丈余,腰围合抱,树龄五百岁之多。庙内有青石碑近百通,高的丈余,矮的七八尺,高碑乌龟相驮,低碑石座固定,仅正殿的陪殿里就有矮碑六排三十通。传说在石碑上摩擦馒头,小孩吃了能顺利长大成人,可免灾不死。所以,每当三月三、六月六庙会之际,或春节、元宵节期间,四乡八邻的香客,赶庙会的人们便带着小孩来到庙中磨馒头,久而久之,殿内石碑被磨得光亮,可以当镜,碑上的字迹也就辨认不清了。庙内碣高碑多,号为碑林,声名远播。庙堂东依起伏小丘,西临盆湖,周围数条逶迤小渠,丘青水秀,别具特色。尤其阳春、仲秋之时,百花争艳,风和日丽,千鸟竞唱,宛若仙境。每当此时,富豪乡绅,纨绔子弟,文人雅士,墨客骚人,常常来此踏青游玩,观赏庙景,结社吟诗,故有“吟社”之名。 清代诗人杨祥云为之题诗曰:“驱蝗德意足千秋,社鼓年年祀子悠。但欲斯民沾雨露,不辞万乘广巡游。”
然而,“吟社”之名阳春白雪,在村民中难免曲高和寡,不如“饮社”来得酣畅淋漓。因此,村民便对商高宗庙赋予更多“饮”的元素,一些关于“饮”的传说浮现,仿佛没了美酒琼浆,商高宗庙便无法匹配“崇岗饮社”之名,也印证了李白那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盆湖成追忆,古庙迹难寻
45岁的李玲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平时就喜欢习文阅史,作为宋岗村村民,对于“崇岗饮社”的历史自然非常关注。她曾听爷爷提起过,爷爷年轻时,每当夜深人静,站在商高宗庙的庙台上,能听到盆湖那边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声音。后来她又询问了多位老人,他们都说有类似经历。
李玲觉得这过于神奇,她猜测那些声音或许是当时环境的某种共振,不过也无从考证了,而商高宗庙却在她记忆中留下清晰印象。“我小时候庙宇还在,红墙绿瓦,亭台楼榭上的画栩栩如生,只是里面的高宗、真武大帝、东武大帝神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或砸烂或付之一炬,只留下空空的庙宇和光滑的石碑。北大庙后来变成了梁庄村小学,2000年以后梁庄小学合并到别的学校,这里年久失修,就更荒芜了。”李玲告诉记者。
自“文革”期间被损毁以来,商高宗庙渐渐变成一堆瓦砾,乃至一片屋舍和耕地。事实上,商高宗庙所在的那片土地属于宋岗村北面的殿高村(村名似与商高宗庙亦有关联)。殿高村76岁的王国顺老人向记者讲述:“我小的时候,商高宗庙很大,起码有10亩地。庙里香火鼎盛,每年农历正月十九、三月三、六月六都要举办香烟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烧香祈福。庙院内椿树榆树柏树都很大,有的树几个人才能抱住。庙内有春秋殿、三清殿、娃娃殿等,楼宇众多。商高宗神像有3.5米高,石碑也有数十块,巨大的龟驮碑,顶部有龙纹。后来‘大跃进’,一些石碑被拿来修桥、盖房子,‘文革’时又遭到进一步毁坏,逐渐消失了。”如今,王国顺老人还保留着一本当年从石碑上手抄下来的《重修观音堂记》,他将之珍藏,算是对古庙的一种纪念。
殿高村76岁的高自华曾在原郾城区文化局工作,他对于这座古庙也有着鲜明的记忆,他说:“庙里确实有很多石碑,大多已损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块断碑,上面记载着这座庙始建于汉元光二年。”对于盆湖,两位老人都表示,小时候便已种上庄稼,只是地势低洼,经常积水。
通过村民的讲述,记者仿佛亲身游历了那巍峨的古庙、神奇的盆湖,但是走出传说,站在曾经的“崇岗饮社”之地,豪饮的神仙难寻身影,吟诗的才子也难觅踪迹,只有夕阳洒下橘色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