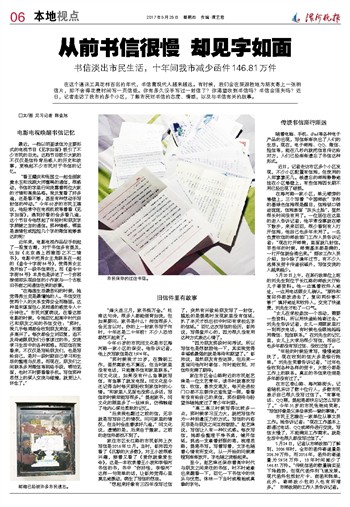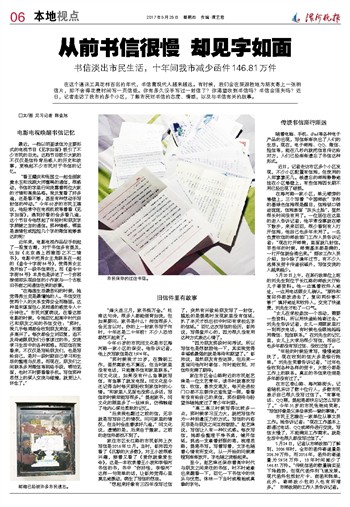在这个通讯工具花样百出的年代,书信离现代人越来越远。有时候,我们会在旅游胜地为朋友寄上一张明信片,却不舍得花费时间写一页信纸。你有多久没手写过一封信了?你渴望收到书信吗?书信会消失吗?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的多个小区,了解市民对书信的态度、情感,以及与书信有关的故事。
□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电影电视唤醒书信记忆
最近,一档以明星读信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见字如面》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这档节目吸引大家的不仅仅是信件背后感人的历史和故事,更唤起不少市民对于书信的记忆。 “看王耀庆和张国立一起念画家黄永玉和戏剧大师曹禺的通信,很感动,书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两位大家的才情和高贵品格。我反复看了好多遍,还是看不够,甚至有种想动手写封信的冲动。”今年60岁的市民王建说,他经常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见字如面》,遇到好看的会多看几遍,这个节目令他想起了年轻时和朋友字字肺腑之言的通信。那种情感,哪里是表情包或短短几个字的微信能够表达的呢? 近年来,电影电视作品似乎刮起了一股复古潮,对于书信多有提及,比如《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电影中把男女主角联系在一起的《查令十字街84号》,使得男女主角开始了一段书信来往。而《查令十字街84号》本身也是讲述了一个穷困潦倒却乐观自信的小作家与一个古板旧书商之间通信往来的故事。 “在海莲生活最苦闷的时候,她觉得弗兰克是最懂她的人。书信交往使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安全而稳固。这种虽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感觉令人十分神往。”市民刘夏萌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令她回忆起高中时代自己和朋友之间的书信交往:“那时,我几乎每周都会收到朋友来信,别提多高兴了。每次都会立刻回复,迫不及待地跟朋友们分享读过的书,交流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困惑。而回信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写给朋友们,也是写给自己,是对一段时期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整理与反思。而现在,朋友们之间联系多用微信等网络手段,哪怕见面,也时不时要看看手机。写信那种思想上的深入交流与碰撞,就更让人怀念了。”
旧信件里有故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这句诗,很多人都能倒背如流,但如果要问:家书是什么?相信很多人会无言以对。你的上一封家书写于何时,十年还是二十年前?不少人恐怕都想不起来了。 今年65岁的市民闫文化是市区海河路一家小区的保安。他告诉记者,他上次写家信是在1974年。 “那时候我才22岁,在舞钢工作,虽然离家也不算远,但当时家里没有电话,只能靠书信和家里联系。”闫文化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就写信,有急事了就发电报。闫文化至今还记得当时每天期盼收到家信时的心情。“和家里人见面也没那么多话,写信的时候却能写很多。”提起家书,闫文化的眼里多了一丝神采,仿佛触碰了他内心深处柔软的记忆。 “后来我也翻过之前的信,无非就是写写自己的情况,问问家里的情况,但当时会连着读好几遍。”闫文化说,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搬家,之前的老信件都找不到了。 家住市区长江路的市民彭帅上次写信是2016年12月。当时,彭帅因为看了《沉默的大多数》,对王小波很感兴趣,接着又看了《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是一本收录着王小波和李银河书信的书,书中“你好哇,李银河”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让彭帅觉得心里莫名地激动,萌生了写信的想法。 “想起来好像有三四年没写过信了,突然有兴致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尴尬的是提笔时发现家里没有信纸,扒了半天才找出初中时印有学校名字的信纸。”回忆这次写信的经历,彭帅说,写得蛮开心的,因为很久没有用这种方式表达心情了。 “因为朋友那段时间考试,所以写信也是想鼓励他一下,其实我觉得幸福感最强的就是等待和期望了。”彭帅说,虽然朋友有些诧异,但后来一直询问他何时寄信、何时能收到,对信件充满了期待。 家住市区金山路附近的市民赵艺琳是一位文艺青年,读书时就喜欢写信、收信,喜欢交笔友,每天走进校门口都不忘朝传达室张望一眼,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来信,那份期待与盼望伴随她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高二高三时候写得比较多一点,那时候学习压力大,就把写信作为一种排遣压力的方式。写信的内容无非是与朋友之间互相鼓励。”赵艺琳说,写信让人有一种仪式感。每次写信,她都会整理干净书桌,铺开信纸,挑选一支拿着舒服的笔,梳理思路,提笔书写。写着写着,文字也随着心情有所变化,从一开始的问候寒暄到渐渐放开,字也随之流畅起来。 至今,赵艺琳还保存着高中时代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书信,时不时地拿出来翻看一下,回忆一下书信中的快乐与忧愁,体味一下当时或稚拙或真挚的字句。
传统书信渐行渐远
随着电脑、手机、iPad等各种电子产品的出现,写信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电子邮箱、QQ、微信、短信等,能在几秒内就把信息传达给对方,人们已经渐渐遗忘了书信这种形式。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发现,不少小区配置有信箱,但使用的人却寥寥无几。被遗忘的邮箱静静地挂在小区墙壁上,有些信箱因长期不用已经出现了破损。 在海河路一家小区,单元楼旁的墙壁上,三个写着“中国邮政”字样的墨绿色信箱很是醒目,信箱锁口锈迹斑斑,信箱表面“灰头土脸”,显然很长时间没有用了。一位居住在这里的老人告诉记者,他平常没事就在楼下散步,来来回回,很少看到有人打开信箱,他自己也多年未用了。一名负责收信的邮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打开邮筒,里面就几封信。早些年的时候,邮筒基本都是满的,一打开信就会涌出来。”据该工作人员介绍,如今除了逢年过节,有不少人选择发贺卡传递祝福外,写信交流的人越来越少。 5月20日上午,在某行政单位上班的刘先生到位于长江路的邮政大厅给儿子寄资料。他一边填着收件人地址,一边用电话跟女儿确认。“原件和复印件都放进去了,复印两份够不够?”填好地址和收件人,交完了快递费,刘先生才松了一口气。 “女儿在学校参加一个活动,需要一些资料,所以用快递给她寄过去。”刘先生告诉记者,女儿一周跟家里打一到两次电话,有时候也会跟她妈妈用微信、短信联系。”在刘先生的记忆里,女儿上大学后很少写信,而自己也多年都没有写过信、没收过信了。 “年轻的时候经常写,慢慢地就淡了,现在收到的信大多是银行账单。”刘先生笑着告诉记者,“过年也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贺卡,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联系。真正的书信来往倒是多年都没有过了。” 在市区泰山路、海河路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数十位行人,多数市民表示自己很久没写过信了。“有事电话、QQ聊,提起笔都快忘记怎么写字了。”今年31岁的市民张艳纯笑称,“写信好像是父亲母亲那一辈的事情。” 市民王艺璇在一家单位从事文员工作。她告诉记者:“现在工作基本上都通过电话、QQ或邮件进行交流,写信太慢了,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就是生活中也很久都没写过信了。”5月24日,记者从市邮政部门了解到,2006年时,全市的函件寄递量是206.39万件,而2016年,函件的寄递量为59.58万件,10年时间减少了146.81万件。“传统信函的数量确实呈下降趋势,但现代函件则飞速发展。现代函件包括封片卡、商函和账单。此外,寄邮政小包的人也有所增多。” 市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