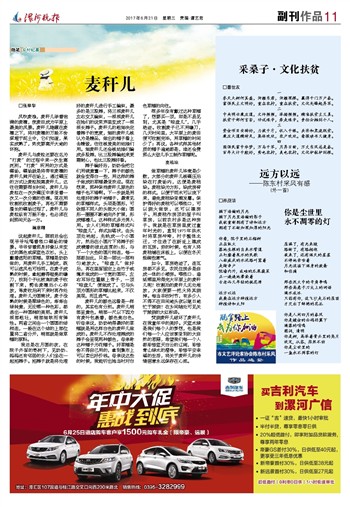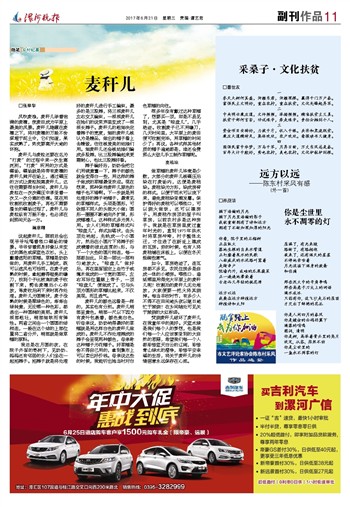□张翠华
风吹麦浪,麦秆儿举着饱满的麦穗,使麦田成为平原上最美的风景。麦秆儿隐藏在麦穗之下,将对麦穗的万般不舍深埋于泥土中,它们知道,果实成熟了,终究要离开大地的怀抱。
麦秆儿与麦粒还要在名为“打麦”的过程中来一次生离死别。“打麦”所用的方式是碾场,碾场就是将带有麦穗的麦秆儿摊开在场上,通过碾压的方式让麦粒脱离麦秆儿,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麦秆儿与麦粒在一次次碾压中承受着一次又一次分离的伤痛。现在用收割机收割麦子,再也不需要漫长的碾场过程了,麦秆儿与麦粒纵有万般不舍,也必须在刹那间天各一方。
编草帽
说起麦秆儿,眼前总会出现爷爷吆喝着牲口碾场的情景。爷爷穿着那身好像从未变过的黑色或深蓝色衣衫,头上戴着遮阳的草帽。草帽是奶奶做的,用麦秆儿手工制成,既可以遮风也可挡雨。在麦子成熟的时候,拿起磨得锃亮的镰刀,找到个子比较高的麦子收割下来,剪去麦穗后小心存放,等麦收后闲下来时再作处理。麦秆儿为圆筒状,麦子没熟的时候是翠绿色的,渐渐由绿转黄,无论哪一种色彩,都透出一种圆润的美丽。麦秆儿根部粗壮,梢部细软而有弹性。两者之间由一个圆圆的结相连,一般在这个结的上部位置将二者分开,梢部就是做草帽的原料。
我总是在月圆的夜,在院子外面的枣树下,见奶奶、妈妈还有邻居的女人们坐在一起掐辫子。掐辫子就是将处理好的麦秆儿进行手工编织,最多的是三股辫,将三根麦秆儿左右交叉编织,—根根麦秆儿在她们的说笑声里变成了一根根长辫子。麦秆儿的粗细决定着辫子的宽度,细的麦秆儿被认为是精品,做出的帽子看上去精致,往往被爱美的姑娘们用。细麦秆儿还会被姑娘们编成多股辫,比三股辫编起来更需耐心,也比三股辫好看。
辫子编好后,奶奶会把它们用硫黄薰一下,辫子的颜色就会变得白一些,用这样的辫子做成的草帽最受欢迎。现在想来,那种保持麦秆儿原色的帽子也不错啊。下一步就是用处理好的辫子衲帽子,最常见的草帽样式,头项是圆形,可依据不同人的头部大小做;圆形一圈圈不断地向外扩展,形成帽檐儿。这种样式多为男人用。女人们用的草帽样式叫“晾盘儿”,样式如塔状,由头顶处衲起,先纳成一个小圆片,然后在小圆片下将辫子折成横着的彼此连贯的s形,与下一个大些的圆片相连,每一层都如此,只是一层比一层均匀地放大。“晾盘儿”做好后,再在里面固定上由竹子或薄木做成的一寸宽的圆环,左右耳际位置缀上带子,一顶“晾盘儿”便做成了。它与头顶为圆形的草帽比起来,不仅美观,而且透气。
麦秆儿的颜色远看是一样的,其实也有分别。麦秆儿梢部呈黄色,梢部一尺以下因为有麦叶包裹着,颜色亮白色。听母亲说,奶奶衲得最好的草帽就是用这样白色的麦秆儿做成的。麦秆儿不作处理辫成的辫子会呈现两种颜色,母亲称这种帽子为花帽子。好草帽是舍不得自己用的,拿到集市上可以卖出好价钱。母亲说这些的时候,我能听出她当时对白色草帽的向往。
很多年没有戴过这种草帽了,想要买一顶,却是不易见到,尤其是“晾盘儿”,几乎绝迹。收割麦子已不用镰刀,几天时间里,大平原上的麦田便可收割完毕,用草帽的时间少了;再说,各种式样其他材质的帽子遍地都是,谁还会费那么大劲儿手工制作草帽呢。
麦秸垛
做草帽的麦秆儿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的麦秆儿被碾压后垛在打麦场内,这便是麦秸垛。麦秸垛为方形,垛成房脊的样式,以便于雨水可以流下来,避免麦秸垛受潮发霉。保护得好的麦秸可以喂牲口,可以烧火做饭,还可以建房子。用麦秸作房顶的屋子叫草房,以前农村多是这种房子。我就是在草房里度过童年时光的,直到1975年洪水时将草房冲垮,村子整体北迁,才住进了在新址上建成的瓦房。穷的时候,也有人将麦秸铺在床板上,以便在冬天抵御些寒气。
如今,草房绝迹了,连瓦房都不多见,农民住房多是自成一体的小楼房。喂牲口、造纸哪里用得完大平原上的麦秆儿呢?收割后的麦秆儿无处堆放,大家便要一把火将其烧掉。每当丰收时节,有多少人不得不在田间地头夜以继日地忙于禁烧?在乡间随处可见关于禁烧的大红标语。
焚烧麦秆儿破坏了麦秆儿在我童年中的美好。天蓝水绿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享受到的大自然的恩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蓝天白云的辽阔,珍惜青山绿水的澄净,珍惜平安幸福的生活,将关于麦秆儿的诗情画意永远保存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