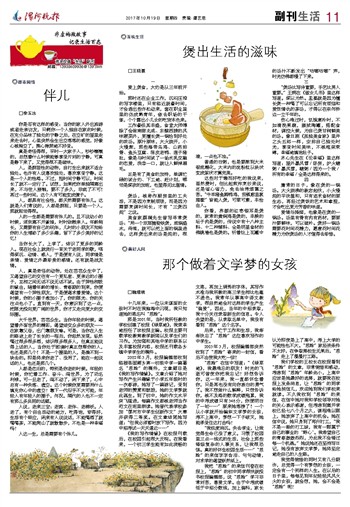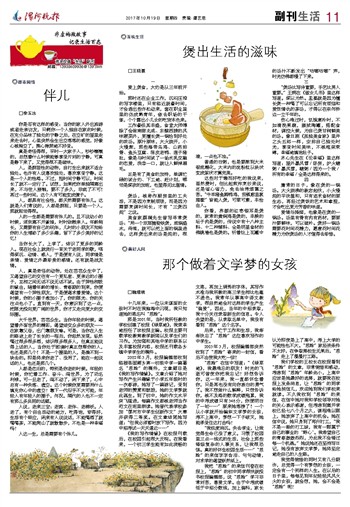□王晓景
一
爱上煲食,大约是从三年前开始。
那时还在企业工作,沉闷压抑的写字楼里,只有临近就餐时间,才会透出些许松动来,套在职业装里的伪成熟青年,敛去职场的干练,个个露出小儿女的吃货本色来。
工作餐极其丰盛,食堂大师傅除了会做南甜北咸、东酸西辣的风味硬菜外,更擅长煲一锅恰到好处的浓汤。原汁原味,大火烧开,小火慢熬,那些海带乌鸡、山药排骨、鱼头豆腐、陈皮老鸭、莲子猪肚,像是与时间谈了一场水乳交融的恋爱,浅尝一口,就让人鲜掉眉毛。
正是有了美食的加持,单调忙碌的谈合约、下工地、赶计划,哪怕是深夜的加班,也显得无比温情。
二
煲汤,被称作厨房里的工夫活,不是因为烹制烦琐,而是因为需要烹调时间长,才有“三煲四炖”之说。
美食家蔡澜先生曾写寻常煲汤:“用一个双层搪瓷铁煲,底锅盛水,待滚,就可以把上面的锅装进去,这样煲出来的汤是炖的,很清,一点也不浊。”
普通的白粥,也是要熬到大米彻底糊化,大米内的淀粉粒从块状变成絮状才算完美。
这些对于懒而好吃的我说来,虽然费时,但比起煎炸烹炒来说,还是省心省力,免去油烤烟熏之苦。“牛羊猪鱼鹅鸭鸡,茄瓠葱韭菰菔藜”皆能入煲,可荤可素,丰俭由人。
你看,养颜的红枣银耳是煲的,家常的黄焖鸡是煲的,丰腴的坛子肉是煲的,传说中有十八种主料、十二种辅料、全是明星食材的佛跳墙也是煲的。听着灶上瓦罐中的汤汁不断发出“咕嘟咕嘟”声,时光仿佛都慢了下来。
三
“煲汤比写诗重要,手艺比男人重要。”王朔在《致女儿书》里这样写道。深以为然。孟婆就是因为擅长煲一种喝了可以忘记所有烦恼和爱恨情仇的茶汤,才得以在奈何桥边一立千年的。
伤心难过时,饥饿寒冷时,不如清洗果蔬,擦拭陶罐,搭配食材,调控火候,为自己煲甘润鲜美的汤。像日剧《孤独美食家》里井之头五郎一样,安排自己独处时光,享受时间美味,不被框架束缚,幸福地填饱肚子。
木心先生在《论幸福》里这样写道:屋外暴风雪∕卧房,炉火糖粥∕暴风雪,糖粥∕因为一个我∕所有的幸福∕全是这样得来的。
四
庸常的日子,像在煲的一锅汤。大火烧沸的跌宕起伏,小火慢炖的平淡温和,只有追求食材的原生态,再经过煲饭的艺术和拿捏,才会吃出更为芳香的味道。
爱情与婚姻,也像是在煲的一锅汤。汤里有骨有肉有药材,要原汁要鲜味,可以滋补。煲好一锅汤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为你煲汤的人才值得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