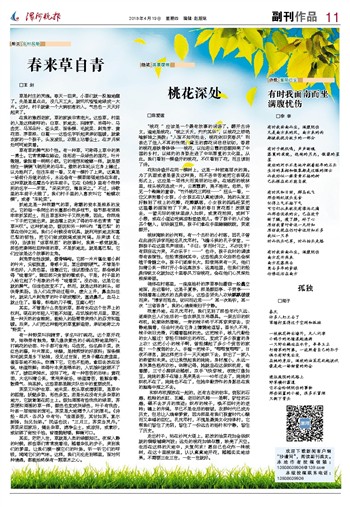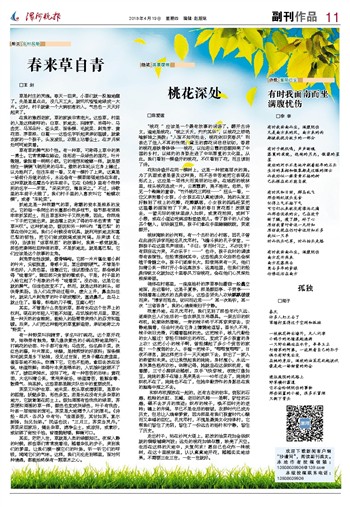□陈爱莲
“桃花 ”应该是一个最有故事的词语了。翻开古诗文,遍地是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花之娇艳喻新娘之美貌;“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则表达了佳人不再的怅惘;黛玉的葬花词悲悲切切,香君的桃花扇铁骨铮铮……桃花,以灿若云霞的容颜照亮了中国的乡村,以绰约的身姿走进了中华厚重的文化里。从此,我们看到一棵盛开的桃花,不仅看到了花,而且读到了诗。
花和诗盛开在同一棵树上,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美。为了巩固或者是普及这种美,而不吝辛苦地把它表现在形式上,这应是一项伟大而美丽的壮举。在城西的桃林里,枝头桃花连成一片,云蒸霞蔚,美不胜收。忽然,听见一个稚嫩的童音:“竹外桃花三两枝……”扭头一看,一位父亲抱着小女孩,小女孩正在认真地读诗,她的头发正好触到了枝上的花瓣,花瓣飘落,小女孩的妈妈赶紧把这温馨的画面拍了下来。好美的春日赏花图!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桃林里游人如织,或赏花拍照,或树下小憩,或在小道边吃碗凉粉垫垫底儿。带了孩子的人们会买个糖人,切块豌豆糕,孩子们拿在手里蹦蹦跳跳,笑逐颜开。
桃林掩映的沙河畔,有一个古朴的小村落,因孔子曾在此游历讲学而起名孔沈邓村。飞檐斗拱的孔子学堂,一群孩子在这里书声琅琅:“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许,孩子此时的诵读带有表演性,但经常浸润其中,这些经典文化自然也会深植于骨髓之中。孩子们逐渐长大,即使将来有一天,他们如蒲公英一样打开小伞远离故乡、远离祖国,但我们的经典传统文化就如这十里春风万亩桃花,会在他们心灵深处根深蒂固。
徜徉在村落里,一座座拙朴的茅草亭如蘑菇一般矗立地面,走近看时,这是子夏亭,那是颜回亭、子贡亭……伴随着高山流水的古典音乐,这些圣贤先人衣袂飘飘缓缓而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再一次聆听,再一次“三省吾身”,我的心境渐渐归于宁静。
很意外地,在孔沈邓村,我们见到了那些年代久远、逐渐淡出人们生活的一些农耕及日用器具。一架古旧的织布机,轮廓依然清晰,一旁的梭子终于不再穿来穿去,安静地躺着,任由时光在它身上慵懒地逗留。虽长久不用,梭子依旧光滑,闪耀着温润的光。这把梭子,被几代勤俭的女人握过?穿经引纬织出的布匹,变成了多少孩童的身上衣?这把小小的梭子啊,曾经撑起了多少个贫苦的家庭?一个瘦弱的女人,手握一把梭子,“唧唧复唧唧”,日夜不停息,就这样把日子一天天地织下去,织出了一家人的希望和未来。这让我想起我的姥姥,身材瘦小,永远一身灰黑色粗布衣衫。依稀记得,她就坐在这架织机前,弯着腰,三寸小脚踩动踏板,双手飞快穿梭,夜晚灯盏如豆,姥姥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40年过去了,姥姥的织机不在了,姥姥也不在了,但她辛勤劳作的身影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和织布机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古老的纺车,斑驳的石磨,粗釉的水缸、瓦罐,老旧的风箱……是啊,驴拉的石磨,碾不去岁月的痕迹;织布的梭子,唤不回时光的逆转;辘上的井绳,早已不是生活的枷锁,农耕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总让人魂牵梦萦,因为那里有我们孩童时代心酸而又幸福的回忆。孔沈邓村,不愧是最美文化传承村,它帮我们留住了光阴,留住了一份远古的拙朴和宁静,留住了历史。
走出村子,站在沙河大堤上,怒放的油菜花如金线织就的绸缎铺满河坡;远处的桃花如锦似霞,映亮了天空。生活在这样的天地中,夫复何求?愿自己也化作一株桃树,在这十里桃林里,认认真真地开花,踏踏实实地结果,不需要三生三世,一生一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