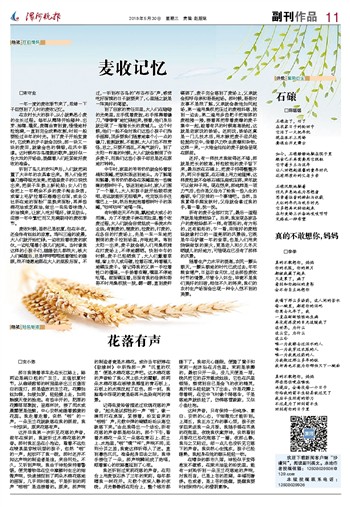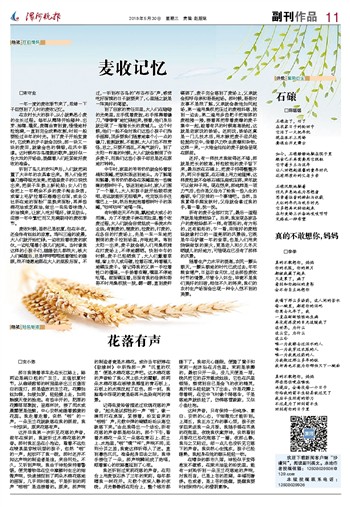□宋守业
一年一度的麦收季节来了,思绪一下子回想到了儿时的麦收记忆。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熟悉小麦的生长过程。每年从霜降开始播种、出芽、抽穗、灌浆,麦穗由青到黄,慢慢地籽粒饱满,一直到完全成熟收割,时间一般要经过半年的时光。到了麦子开始变黄时,它成熟的步子就会加快,那一块又一块的麦田,就像金色的绸缎,在风中荡漾。这时候布谷鸟清脆的歌声,就好似一台大戏的开场曲,提醒着人们赶紧做好麦收的准备。
听到了鸟儿的欢叫声后,人们就把闲置了大半年的农具拿出来。男人们会把镰刀磨得锃光发亮,把盛装麦子的口袋找出来,把架子车换上新轮胎;女人们也会把上一年剩余不多的麦子淘去杂质,或套上毛驴拉着石磨磨出白面,或去公社所在地的面粉厂里换来面粉,再弄些棉花油或芝麻油,做出一张张香味馋人的油馍来,让家人吃好喝好,铆足劲头,迎接一年中繁忙而又充满期待的麦收季节。
麦收时候,虽然已是初夏,但在半夜,还会伴有丝丝的凉意。鸡叫三遍的凌晨,大人们就开始忙碌,一边收拾着收麦的家伙,一边吆喝着小孩儿们起床。当时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们,瞌睡劲儿都很大,被大人们喊醒后,总是哼哼唧唧揉着惺忪的睡眼,很不情愿地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不过,一听到布谷鸟的“布谷布谷”声,感觉吃好面馍的日子就要来了,心里随之就是一阵美好的渴望。
到了自家的责任田里,大人们在暗暗的光亮里,左手揽着麦拢,右手挥舞着镰刀,“噌噌噌”地忙碌起来,接着,他们身后就出现了一溜溜长长的麦铺儿。这个时候,他们一般不会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指手画脚,顶多要我们随意地拿个小一点的镰刀,能割就割,不能割,大人们也不很责怪,总之,只要不捣乱,不淘气就行。到了太阳一杆高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割倒了许多麦子,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总是还在原地打转转。
中午时,家里的爷爷奶奶就会拎着饭桶和茶罐,把饭和茶送到地头。为了解渴和解暑,爷爷奶奶都会在茶罐里泡一些嫩嫩的柳树叶子。饭送到地头时,家人们围了一个圈儿,大人和孩子就开始狼吞虎咽,老远就能听见咀嚼声。吃完饭后手往嘴巴上一抹,然后抱起泡着柳树叶子的茶罐,“咕咚咕咚”地喝一阵。
有时候老天不作美,飘起或大或小的雨滴。为了不使麦子淋在雨肚里,整个收麦过程,大人们就会自觉组成一条流水作业线,有割麦的,捆麦的,拉麦的,打麦的,在各自的打麦场上,先是一车一车地把割倒的麦子拉到场里,并堆起来。等到太阳一出来,麦子就会被人们用桑杈摊在打麦场上,不停地翻晒。快到中午的时候,麦子已经晒焦了,大人们戴着草帽,套上牛儿或马骡,拉着石滚,转着圈儿地碾压麦子。曾记得我的父亲一手拉着牲口的缰绳,一手扬着皮鞭,嘴里不停地吆喝。前面碾压着,后面有我的母亲和哥哥不时用桑杈挑一挑,翻一翻,直到麦秆碾碎了,麦子完全落到了麦场上,父亲就会招呼母亲和哥哥起场。那时候,哥哥对农事不是很了解,父亲就会教他如何起场,第一遍用桑杈把压过的麦秸抖落,挑到一边去,第二遍用多齿耙子把细碎的麦秸搂一搂,接着再把带着麦糠的麦子集中一起,趁着有风的时候高高扬起,这就是老家说的扬场。还别说,扬场还真是一门儿技术活,用木锨把麦子迎风轻轻抛向空中,借着风力吹去麦糠和杂物,这样一来,一大堆金灿灿的麦子就会呈现在眼前。
还好,有一样技术我做得还不错,那就是把长的较高,籽粒较饱的麦子留下来,最后放在石磙上,把麦子捋得整整齐齐,两只手握紧,在石磙上用力地猛摔,这样麦粒就不会被石磙压扁或压碎,来年就可以做种子用。现在想来,那纯粹是一项力气活,也许是父母为了给我一些人生的磨砺,专门安排的一个事情吧。当然,当我累得手脚发软时,父母就会拿过我的手,看一看,抚一抚。
所有的麦子全部打完了,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堆麦秸垛了。后来,我发现各家各户的麦秸垛都不一样,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船形的,乍一看,刚堆好的麦秸垛就像村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既是牛马驴骡一年的食草,也是人们用来烧锅做饭的柴火,更是老人和少儿冬天晒暖儿的好地方,可惜现在已没有了那样的风景。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一撅头朝天,一撅头朝地的时代已成过去,年年粮食增产,日益衣食无忧,过去那些麦收时节的情景,尽管令人怀念,毕竟不是我们美好的归宿,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农村生产场面会出现一种令人想不到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