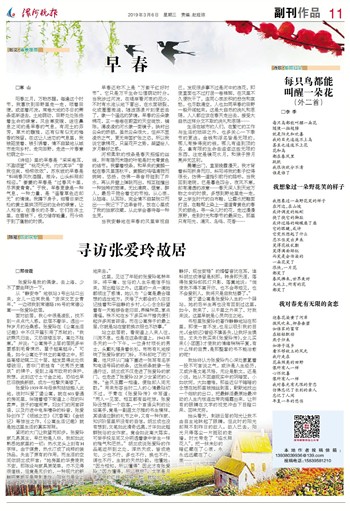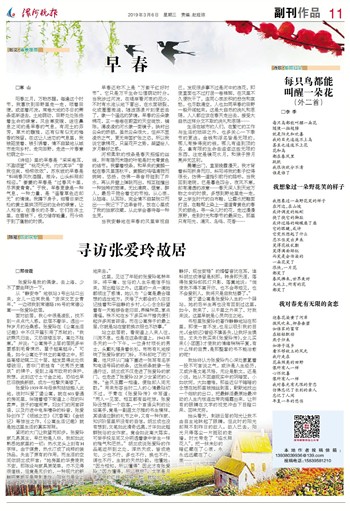□邢俊霞
张爱玲是我的偶像,去上海,少不了要去拜访一下。
从“静安寺”地铁站3号出站口出来,女儿一边笑我是“资深文艺女青年,”一边领我到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张爱玲故居。
面对故居,我心中很是凌乱,找不到一点点代入感。故居不奢华,透出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不仅开篇引用了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并说:“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可是,如今公寓处于林立的高楼之中,那些高楼动辄二三十层,越发显得此处低矮破旧,若非门前挂有“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受到上海市政府的保护,我想,此刻这寸土寸金之地,恐怕也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一柱擎天高楼了。
张爱玲1939年与母亲和姑姑搬入此地,彼时叫爱丁堡公寓,就在605普通的房间里,伴随着楼下街道上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喧闹声,妇女们的闲言碎语,以及行进中电车嘈杂的铃音,张爱玲创作了《倾城之恋》《沉香屑》《金锁记》等惊世之作,《公寓生活记趣》就是她这里生活的真实写照。
紧闭的大门让我望而却步。张爱玲家几易其主,早已物是人非,我却如此熟悉她家里的一切:热水龙头上刻有H字样,由于煤贵,热水汀成了纯粹的装饰品,失去了原有的作用,而生活的空间依胡兰成所言:“她房里的华贵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
这里,见证了年轻的张爱玲笔耕年华,将平庸、世俗的人生乐趣信手拈来,写出超俗之外。这里的一点一滴她都倾注了感情,她认为“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站立故居前,看街道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也是在这条街道上,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身材颀长的男士,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彬彬有礼地按响了张爱玲家的门铃,不料却吃了闭门羹,他只好从门缝下塞进一张写有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条,这张纸条就像一张通行证,胡兰成不仅走进了张爱玲的家门,也走进了张爱玲22岁少女紧闭的心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用来形容当时二人的心情最贴切不过,于青在《张爱玲传》中写道:“两人一见面,相互都有些吃惊。张爱玲没想到一个政客,一个言语尖利的论坛高手,竟是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其诺诺应酬的礼节之中,又有一种作家、知识阶层里所没有的自信。胡兰成也没有想到,文笔如此清奇远奥,才华如此超群脱俗的女作家,竟会如此高大笃实,可举手投足间又分明透着像中学生一样的稚气和茫然。”胡兰成说张爱玲的作品笔迹所到之处,浑然天成,皆成绝句,少也不行,多也不行,换也不行,调也不行,生就的天然妙韵。他懂她:“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此才有张爱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文字是月老手中的红线,轻轻一抛,就扯出了一段倾城之恋。然而,好景不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誓音犹在耳,谁料胡兰成停留是刹那,转身即天涯,落得张爱玲却孤灯只影,落寞地说:“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也不会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枯萎了。”
爱丁堡公寓是张爱玲人生的一个驿站,她的后半生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如今,我来了,从千里之外来了,对我来说,这里早就是心灵向往之地。
书柜里张爱玲的著作静静地站在那里,即使一言不发,也足以吸引我的目光。《金锁记》曾经不慎丢失,让我好生懊恼。丈夫为我买来《张爱玲传》,女儿买来《小团圆》才使我的情绪稍稍平复,有什么样的自责,是那整套的书不能治愈的呢?
我始终认为张爱玲内心深处氤氲着一股不可言说之气,或许是人生经历,又或许是文笔风格,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她从不回避现实中的阴暗面,小如坎坷,大如磨难,那些近似于晦暗的念想在她那里被抽丝剥茧,默默地找出一个细软的出口,把最鲜活最原始最冲动的人生内核连血带肉揭露出来,让所有的眼睛在文字的视觉冲击下目瞪口呆、回味无穷。
抬头看天,刺破云层的阳光让我不由自主地眯起了眼睛。但此时的阳光却照不到昨日的故人。故人已去,阳光只得落尘一片斑驳的老墙。时光带走了“临水照花人”,把一抹朱砂的暗红藏在了心底,永永远远藏在了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