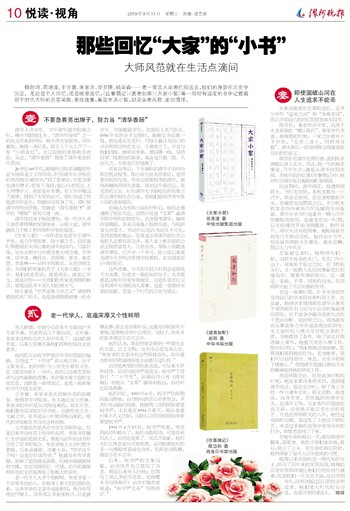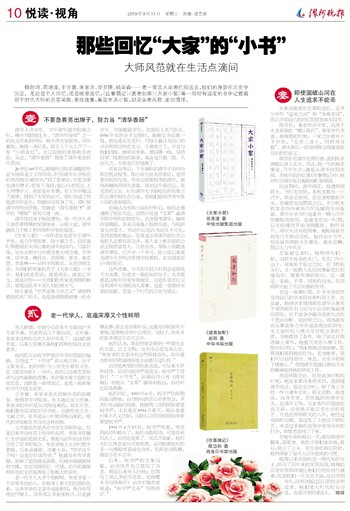梅贻琦、周培源、王世襄、朱家溍、华罗庚、钱学森……老一辈文人学者已经远去,他们的身影在历史中沉淀。无论是个人回忆,还是晚辈追忆,《往事偶记》《逝者如斯》《大家小絮》等一部部有温度的书中记载着那个时代大师的音容笑貌、掌故逸事,虽是生活小絮,却见学者风骨、家国情怀。
壹
不要急着亮出牌子,努力当“清华香肠”
清华人讲究吃。当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时,杨步伟跟随丈夫、“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赵元任来到学校。杨步伟大家闺秀,内外兼修,做得一手好菜,联合几个太太开了一家“小桥食灶”,尤以自制的香肠最受欢迎。从此,“清华香肠”便成了清华美食的代名词。
20世纪60年代,刚刚经历院系调整的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告诫同学:“到了新单位,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要放下身段,虚心向老同志、工人师傅学习。真要是有本事,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你就给母校争了光,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你就是‘清华香肠’!”清华的“硬核”校风可见一斑。
清华依托庚子赔款建校,那一代学人身上肩负着特殊的家国使命。从根上起,清华就致力于做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摇篮。
《大家小絮》一书作者张克澄生于清华世家,是力学家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在大师云集的清华校园内,耳濡目染,从生活和学习中感受着大师之魂。华罗庚、钱学森、林同炎、蒋南翔、常迵、黄克智、季羡林……从科学到教育,从医学到文学,大师们的形象跃然于《大家小絮》一书中。他们或是邻居,或是师长,或是忘年交,或是玩伴……大师们的形象是那样的鲜活,展现出很多不为人知的烟火气。
陆士嘉是“世界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教授的关门弟子,也是普朗特教授唯一的女学生、中国籍留学生,在国际上名气很大。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时,她被定为高教一级,按说是实至名归。可陆士嘉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资历均在沈元、王德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她申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自领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随她了。
恢复高考后,下乡插队的清华子弟纷纷抓住机会报考。陈小悦与张克澄要好,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所有志愿都报考的清华,最终却被陕西师大录取。得知这个情况后,张克澄的父亲、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立即去清华招生办公室,要他们查陕西考生陈小悦的录取情况。
在确认没有陈小悦的材料后,他将此事通报了校长刘达,说明小悦是“文革”前清华附中预科的特优生,此次报考清华,被陕西省截留,并表示准备上报教育部,与陕西省交涉要人。刘达听后也认为此风不可长,支持张维的做法。张维遂亲带清华招生办公室的人去教育部交涉,派人拿上教育部的公函去陕西省要人。几经交涉,等陈小悦踏进清华课堂,已开学一个多月。陈小悦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到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这是作者思忆父母和清华大师的动人故事,也是一首缅怀先辈的颂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与见证。
贰
老一代学人,底蕴深厚又个性鲜明
有人曾谓:中国今后在各个方面出许多专家不难,但要再出几个像启功、王世襄、朱家溍这样的文化人却不容易了。这话的意思是,后来人很难具备他们那样的综合文化素养。
赵珩的父亲赵守俨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主持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由于父辈关系,赵珩同时与三位先生都有交往。在《逝者如斯》一书中,赵珩以沧桑笔墨叙述与这些前辈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既是一部师友记,也是一部浓缩的当代中国文化史。
王世襄、朱家溍是北京城有名的收藏家。他俩并非学院派,有人就此说王世襄、朱家溍的学问是从玩闹出来的,其实不然。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包括经史之学、文献之学,很多是从小时候训练出来的,现代的学校教育多没有这种训练。
王世襄虽然是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但是后来并没有用上所学的东西。朱家溍在辅仁大学读的是国文系,倒是与幼年的读书经历有了更多的契合。朱家溍刚上大学时想学素描,后来余嘉锡、沈兼士说:“你学这个干吗?还是好好读经史。”他就没有再学素描,放弃了走绘画这条路。但他中国画画得相当棒,字也写得很好。可见,幼年的熏陶和所处的文化氛围给了他极大的益处。
老一代学人大多个性鲜明。朱家溍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在他身上看不到包装的色彩。从朱家溍的文章中也能看到,绝没有用理论吓唬人,没有那么多起承转合,只是就事说事,语言也非常朴实,这就为学院派所不重视,觉得他没有什么理论。实际上,朱家溍的很多理论尽在不言中。
赵珩认为,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假大空的文章,言之无物,完全没必要写那么长。“朱家溍的文章没有这些矫揉造作,其中蕴含的知识和道理却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启功是典型的学院派名流,可从来不骄矜自持。启功与赵守俨是故交,赵守俨主持修订“二十四史”,请调启功点校《清史稿》,将他从“文革”漩涡中救出,启功对此很是感激。
赵珩回忆,1993年6月,赵守俨住院期间查出肺癌,启功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他曾两三次到医院看望赵守俨,尤其是在1994年春天,他从香港归来不久又住院,出院后立即扶杖到病房来看望赵守俨。
1994年4月13日,赵守俨病逝,考虑到启功年龄大了,赵珩没敢惊动,可是告别仪式上,启功还是来了。仪式开始前,赵珩夫妇去休息室向大家致谢,启功握着赵珩的手一句寒暄客套话也没有,但却老泪纵横,情谊尽在不言中。
后来,赵守俨的文集出版,启功欣然为之题写了书名。据说后来有人问他:您题写了那么多的书名签,觉得哪本书写得最好?启功不假思索地道:“赵守俨文存”写得最好。”
叁
即使国破山河在 人生追求不能丢
如果说晚辈对长辈的追忆,还多少有些“溢美之词”和“为尊者讳”,那么学者自己的回忆则更加真实自然。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
陈岱孙在清华长期任教,直到院系调整后进入北大。因此,他一生的桃李事业,乃至生活,就是从清华园到燕园。在晚年的回忆集《往事偶记》中,他对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印象颇深。
抗战期间,清华南迁,组建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各机关都有一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在空袭频繁的年头,在城里发出警报之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清华大学当时也备有一辆小汽车供梅贻琦使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贻琦毅然封存汽车辞退司机,每日安步当车,往返寓所和联大办事处。遇有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
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外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乱坟间事前挖好的壕沟中,观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在这一艰难时期,许多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抗战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清华从事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到昆明之后,周培源改而从事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条件。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工作。陈岱孙回忆:“我们和他达成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周培源于是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再说回陈岱孙。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按理说,出身世家,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在清华工作,又拿着四百银圆的高月薪,应该最不能忍受生活的艰苦。可是在西南联大的八年,他住过戏院的包厢,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承受过手稿在战争中化为乌有的打击,却依然坚持了下来。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六点半起床的习惯。
晚清以来中国的这一两代知识分子,经历了百年来的风风雨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让他们历经坎坷与磨难,但是他们一生矢志不渝,从治学到为人,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们是大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晚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