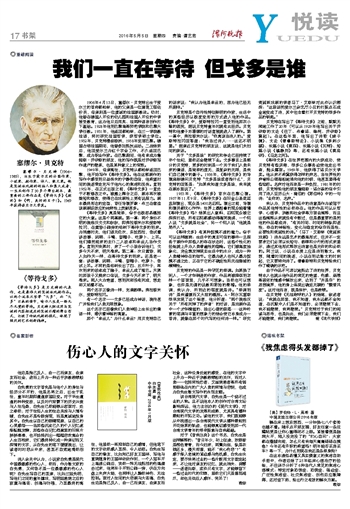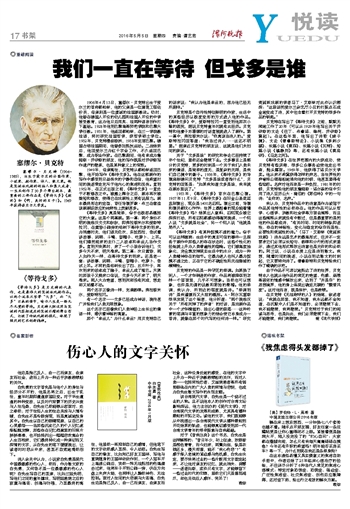1906年4月13日,塞缪尔·贝克特出生于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程估价员,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法国新教徒。幼时,他曾在德国人开设的幼儿园和法国人开设的中学接受教育,这为他日后用英、法两种语言创作打下基础。1928年他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1931年,他返回都柏林,在三一学院教法语,同时研究法国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32年,贝克特漫游欧洲,1938年定居巴黎。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曾参加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他回爱尔兰为红十字会工作,不久返回巴黎,成为职业作家。在巴黎期间,他有幸成为詹姆斯·乔伊斯的朋友,他的写作既是对乔伊斯写作遗产的继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背叛。
1949年,母亲离世,贝克特从都柏林返回巴黎,他开始写作《等待戈多》。他在这部剧作的写作中感受到日益丧失的宁静和自信,他希望时间的流逝带走充斥于他内心的焦虑和沮丧。直到1952年,在正式出版之前,《等待戈多》一直处于不断修改之中。被搬上舞台之后,剧本再次被缩短和修改,使得它在戏剧性上更有说服力。剧本最终形态的定型,首任导演罗歇·布兰在营造该剧剧场效应的纯粹性上贡献甚多。
《等待戈多》真是简单,似乎也极容易概括它的大意。这是个两幕剧。第一幕: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即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黄昏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戈多的到来。为消磨时光,他们语无伦次,东扯西拉,尝试着讲故事、闲聊、斗嘴、耍帽子、吃萝卜、上吊。他们错把前来的主仆二人波卓和幸运儿当作戈多。直到天快黑时,来了一个小孩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第二幕:次日黄昏,两人如昨天一样,在等待戈多的到来。还是老一套:讲故事、闲聊、斗嘴、耍帽子、吃萝卜、尝试上吊。不同的是枯树长出了四、五片叶子,再次到来的波卓成了瞎子,幸运儿成了哑巴。天黑时那孩子又捎来口信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准来。两人大为绝望,想到死却没有死成,想走却又站着不动。
两个名字正像诗一样,充满韵律。弗拉季米尔,爱斯特拉冈。
有一个名字——戈多已经成为神话,流传甚广并给我们人类无限想象。
这个名字已经像我们人类神经上生长出的谶语一样,潜伏着神秘的寓意。
那个“幸运儿”为什么幸运?用贝克特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他是幸运的,因为他已经无所期待。”
贝克特是个自传性特征鲜明的作家,生活中的某些经历以极度变形的方式进入他的作品。《等待戈多》中,爱斯特拉冈一直受到他那双小鞋的困扰,据说贝克特童年时就有此经历。贝克特和他妻子苏珊娜的对话直接就进入了剧作。第一幕中,弗拉季米尔说:“你真该当诗人的。”爱斯特拉冈回答道:“我当过诗人……这还不明显。”据亲近贝克特的朋友说,这就是他们夫妇间的原话。
关于“戈多是谁”的研究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显然还会继续下去。戈多事实上是部分的贝克特,更多的时刻是一个关于我们人类未来的谶语,是简单的虚无,是复杂的无限,是我们自己镜中的影子。1956年,《等待戈多》的导演施耐德问贝克特“戈多是谁或者指什么”,贝克特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戈多是谁,我早就在剧本里说了。”
1953年,《等待戈多》首次在巴黎公演。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观众是1400名囚犯。演出之前,导演和演员都忧心忡忡: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能看懂《等待戈多》吗?结果出人意料,囚犯观众被它深深打动,所有囚犯都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犯人说“戈多就是社会”,另一个犯人说“他就是局外人”。
《等待戈多》有某种捉摸不透的魔力。似乎可以这样臆测:生活中的真实可信的事件一旦服务于剧作中那些人的存在状态时,这些个性化的经验就上升为人类普遍性的隐喻。它们被高度抽象化,完全蒸发掉现实生活中的水分,成为一种人类精神存在的细节。它最为迷人也叫人最为捉摸不透之处,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无法缩减的模糊性。
贝克特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单调。如果换了别人,一个才华稍逊的作家,作品将被降低到怎样一个层面里,几乎不可想象。当然也可以想象,也许是无谓的说教和笨拙的滑稽。他的单调,我认为,所到达的程度就是诗。“单调到诗”是我谨慎而又大胆的概括。A·阿尔瓦雷斯很早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分析道:“两个流浪汉关于‘所有死掉了的声音’的对话,是戏剧作品中一个才华横溢的、独出心裁的段落……这种朴素的笔调与丰富的想象力的结合使它本身成为一首诗,就像在那个时代写的任何诗一样。”研究荒诞派戏剧的学者马丁·艾斯林对此亦认识颇深:“这段话把爱尔兰杂艺厅小丑的打探点石成金地变成了诗,其中包含着打开贝克特的很多作品的钥匙。”
贝克特在写出了《等待戈多》之前,默默无闻地工作了20年(可以从1929年他写出关于乔伊斯的文论《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算起)。在这些年里,他写出了诗歌《婊子镜》、文论《普鲁斯特论》、小说集《多刺少踢》、长篇小说《莫菲》、长篇小说《瓦特》、短篇小说《镇静剂》等,还有长篇小说《莫洛伊》、《马龙之死》。
《等待戈多》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获成功,使贝克特有些厌倦,很多公众事务迫使他走出书斋,抛头露面。196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从来不希冀获得怎样的声名,当世界性的声誉排山倒海般地涌向他的时候,他甚至显得有些恼怒。名声对他而言是一种负担,1981年的时候,贝克特给他的朋友詹姆斯·诺尔森的信中引用了诗人亚历山大·蒲伯的《笨伯咏》中的一句诗:“去你的,名声。”
我认为,贝克特作品中的诗意是作为凌驾于作品其他特性的必然存在。他的作品可以从哲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方面去阐释,而且这些阐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最重要的是把他的作品看成诗,“有关时间、时间的稍纵即逝性、存在的神秘性、变化与稳定的似非而是性、必要性和荒诞性的诗。”(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诗永远是艺术的最高形式,但并不一定要求它们必须以长短句、韵律和分行的形式来显示,通过其他形式释放出诗意也是允许的和必然的。阿兰说,小说在本质上应是诗到散文。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说在到达散文的时刻起,它又要转向诗了。普鲁斯特和贝克特给我们作了精确的示范。
由于作品不可思议地抵达了诗的世界,贝克特本人也就从他作品的常见的绝望、伤感、崩溃等恶劣的情感中解放出来,达到了“齐是非”的思想境界,他的身上体现出确定无疑的“魏晋风度”。这对他而言,既是保护,也是救赎。
在贝克特《无法称呼的人》的结尾,叙述者说:“我就在那里,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在沉默中人们是不知道的,必须继续下去,我不能继续,我将继续。”贝克特对于我们的阅读与思考,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们不能继续,我们将继续。据《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