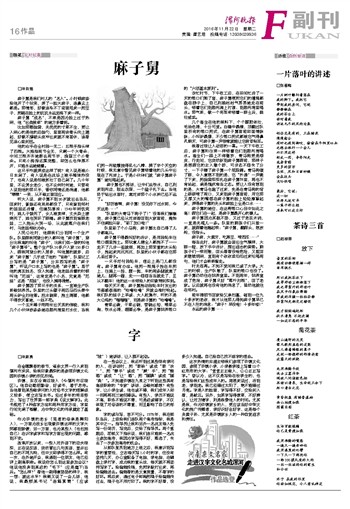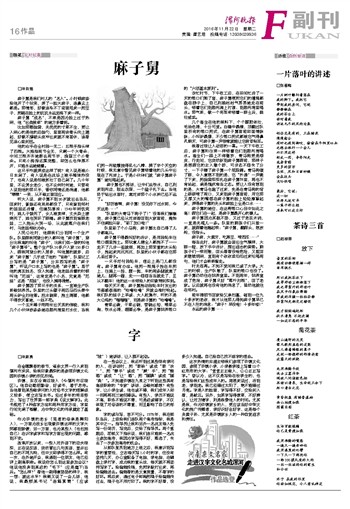□宋自强
麻子舅是我们村儿的“名人”。小时候麻疹给他开了个玩笑,弄了一脸大麻子,连鼻尖上都是。那情形,好像谁冷不丁迎面甩来一把豆子,把砸在脸上的坑坑永远定格下来一样。
麻子舅“成名”,不单是因为脸上过于热闹,他“出类拔萃”的地方多着呢。
比如那颗脑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更让人闹心的是他的后脑勺,里面两块骨头向上翘起,好像不撑破头皮冲出来就不肯罢休,谁看见谁心里别扭。
他的右手在全村独一无二:五根手指头掉了四根。大拇指两节全无,只剩一个大骨朵;中间三根齐齐地断去两节半,残留三个小骨朵。只有小拇指还算完整,却怎么也伸展不开,只能永远地蜷着。
这只手咋就弄成这样了呢?有人说是被小日本剁了,有人说是在战场上被手榴弹炸没了,也有人说是怕被抓壮丁自己剁了。几十年里,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说到他的那只手,管你同情还是消遣,他都“嘿嘿”一笑,从不做正面回应。
听大人说,麻子舅不到20岁就出去当兵,回来时,爹娘还有弟弟都没了,只有嫁到邻村的姐姐还活着,但境况凄凉:1942年闹饥荒时,她儿子饿死了,女儿被卖掉,丈夫染上痨病死了,她也哭坏了眼睛。麻子舅找到盲眼老姐,二人抱头大哭一场,从此就落户在我们村,与老姐相依为命。
人民公社时,他跟我们分到同一个生产队。队里跟我同辈分的人都叫他“麻子舅”,辈分比我高的叫他“麻子”,比我们低一辈的叫他“麻子舅爷”。整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150多口人,跟我同辈分的人居多,叫他舅的就多,后来“麻子舅”几乎成了他的“官称”,队里记工分写的是“麻子舅”,分东西写的是“麻子舅”,听说户口本上写的也是“麻子舅”。至于他的真实姓名,没人知道,他老姐活着的时候叫他“尼娃”,这肯定是个小名,究竟是“尼娃”还是“泥娃”,也没人搞得清楚。
麻子舅因了那只手的关系,一直被生产队派做饲养员。队里的三头骡子两匹马四头耕牛两头驴全归他管。担水铡草,推土清圈,他都干得欢天喜地,一丝不苟。
一个玉米棒子刚刚长出天英的傍晚,我和几个小伙伴赤条条地在颍河湾里打水仗,当我们把一河晚霞搅得乱七八糟、溅了半个天空的时候,我无意中瞥见麻子舅领着他的几头牛出现在了河岸上。于是小伙伴们就“麻子舅麻子舅”地吆喝起来。
麻子舅也不搭话,让牛们去饮水,自己则来到河边,脱去衣服,一个猛子扎下去。当他终于钻出水面时,离对岸那个小水洲已经不远了。
“好厉害啊,麻子舅!没见你下过水呢,今天这是……”
“队里的大青马下驹子了!”没等我们嚷嚷完,麻子舅已经从对岸游回到大家面前,掩饰不住满脸兴奋,“添丁加口啦!”
队里添了个小马驹,麻子舅比自己得了儿子都高兴。
麻子舅干得最叫好的活计,是用独轮车往牲口棚里推土。那玩意儿健全人都推不了——走不了几步一歪就倒,再加上那笨重的木头轮子,推起来死沉死沉,队里的小伙子都在它那儿丢过面子。
一只手对付独轮车,理论上是门儿都没有。麻子舅有办法。他把一根绳子拴在车把上,往肩上一挂,腰一挺,车的两条腿就离了地儿;腿再一蹬,走——稳稳当当就走了,且从不翻车!他的这一本领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每天天不亮,麻子舅推动独轮车时发出的节奏感极强的“咕噜咕噜”声就会准时响起。我们队的娃子上早读、大人赶集市,听的不是大公鸡的“喔喔喔”,而是麻子舅的“咕噜噜”。
青草必嫩,干草必铡,要铡必短,喂草必淘,饮水必清,棚圈必净,是麻子舅饲养牲口的“六项基本原则”。
农忙时节,下午收工后,在田间忙活了一天的牲口们卸了套,麻子舅便把它们的缰绳都盘在脖子上,自己则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头,领着它们到颍河滩上打滚、到颍河湾里喝水。那气派,像一个将军率领着一群士兵,雄壮威武。
几个畜生在他的照料下,个个膘肥体壮,毛油色清,十分可爱。白犍牛最横,顶翻过队里所有的牲口把式,在麻子舅面前却温情脉脉;小叫驴最犟,不少牲口把式都被它气得鼻孔朝天,可麻子舅一声咳嗽就能让它俯首帖耳。
我看过很让人动容的一幕。一天下午收工后,麻子舅和往常一样领着它们到颍河湾喝水。畜生们一路上不停撒欢,青马驹更是顽皮,行走间,它突然跃到麻子舅跟前,那样子是想跟它的主人撒个娇,可步态不稳失了分寸,一下子蹭了麻子舅一个屁股蹲。青马驹傻了眼,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把脑袋深深扎在麻子舅怀里,再也不肯站起,满是愧疚难当之态。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大青马也跑了过来,先是在青马驹的背上狠狠啃了两口,又来到麻子舅面前,用它那又厚又大的嘴唇在麻子舅的脸上轻轻摩挲起来,弄得麻子舅的光头和麻脸上全是口水……
麻子舅的地位,在这帮牲口心目中如此之高!跟它们在一起,是麻子舅最开心的事儿。
麻子舅因为其貌不扬,又过于老实木讷,一直是光棍儿一条。队里的熊孩子们兴致一来,就跟着他瞎起哄:“麻子舅,翻跟头,想放枪,没指头。
麻子麻,大黄牙,吃黑豆,啃西瓜……”
每当此时,麻子舅就会装出生气模样,大眼一瞪,放下手中活计,摆出追击的架势。熊孩子们一哄而散,回头看看没啥危险,又踅回来继续胡闹,直到有个叔叔或伯伯过来吆喝两句,他们才会乖乖溜走。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已读了大学。大二的时候,生产队散了,队里的牲口也没了。麻子舅仍然住在饲养室里。不到两年,饲养室成了危房,麻子舅只好“落叶归根”,回了老家。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虽然他就住在邻村。
前年清明节回家给父亲扫墓,碰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叔,我才从他那儿得知麻子舅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麻子?早没啦!十多年喽!”
永远的麻子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