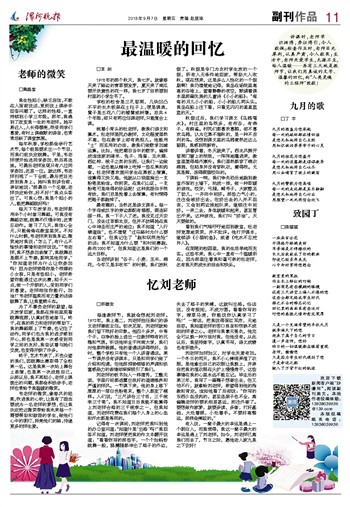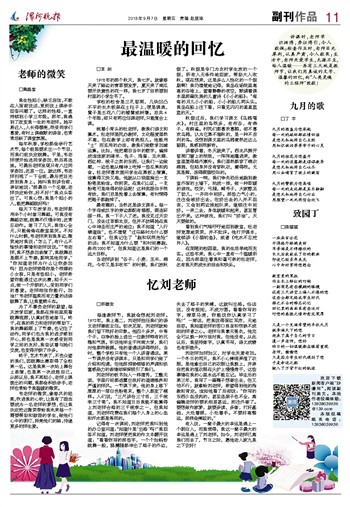□邢德安
每逢教师节,我就会想起刘老师。1972年,我上高二,刘老师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初次见面,刘老师就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四十多岁,中等个子,白净的脸上透出一位教师特有的沉稳和气质。听说他毕业于河南大学,我们对他都很敬佩。他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当时,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人讲普通话。第一节课并没有讲课本,只是和同学们做了介绍和沟通,但他那抑扬顿错的声调和极富感染力的表情却深深吸引了我们。
刘老师的板书如人一样清秀,工整无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严谨的师风。一节课下来,他的身上落下厚厚的一层白色粉笔末,整个人都变了模样。人们说,“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千桃李三寸笔”。我不知道日后我能不能算得上刘老师合格的三千桃李之一,但我知道,刘老师花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血和汗水都是等同的。
记得有一次课间,刘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道:“知道什是‘出格’吗?”我回答不知道。刘老师便把我的作文本翻开说道:“看看你写的那些字,一个个如蚂蚱跳舞一般,胳膊腿都伸出了格子的外边,失去了格子的束缚,这就叫出格。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看看你写的字,潦草马虎,你能说你认真学习了吗?”一席话,把我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我知道老师的苦口良言和恨铁不成刚的师者之心。老师与我素无冤仇,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方法对我,但他没有。从此以后,我坚持练字,认真书写,语文成绩也有所提升。
刘老师如师如父,对学生关爱有加。一个冬日的雨天,我不小心摔倒弄湿了衣服,是他拿出自己的衣服让我换上,并亲自把我的湿衣服在火炉上慢慢烤干,这些事情在我的心里永远不能忘记。毕业后的第三年,我写了一篇稿子想寄出去,但又怕不行,就拿给刘老师,希望得到他的指教和肯定。谁知他看了后却说:“你写的东西少血没肉的,甚至连架子也不全,离编辑老师的要求相差甚远,别往外寄了。要想做作家梦,就要多读,多练,打好基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要好高骛远,那样会摔跤的。”
有人说,一辈子最大的幸运是遇上一个明白人,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是遇上了刘老师。如今,刘老师已离我们而去了,节日之际,愿他老人家九泉之下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