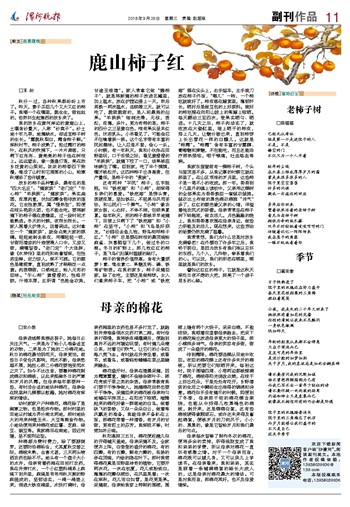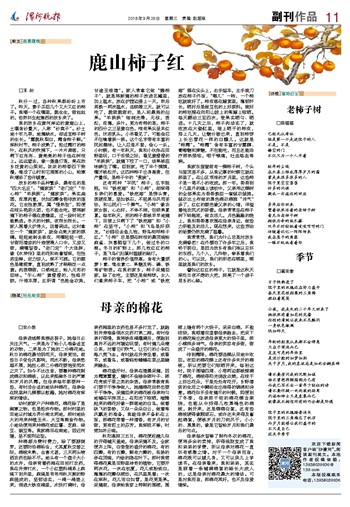□安小悠
母亲进城帮我接送孩子,她每日必关注天气,一来是为了给小儿准备适宜的衣物,二来是为了她的二分棉花地。秋日的棉花最怕阴雨天,母亲更怕。前些日子受台风影响,雨水不断,母亲愁眉不展,她担心那二分棉花要饱受雨水之灾了。如今不比往昔,要靠种棉花制成棉衣和棉被,以此来抵御冬日的严寒和岁月的风霜。但母亲每年都要种一些,有时没合适的地块种棉花,母亲会在院里种几棵聊以慰藉,她对棉花有深深的情结。
幼时家家户户种棉花,棉花除了是御寒之物,也是经济作物。那时村里的田地以村域为界分南北两地,那时地块大的用来种植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小地块便用来种棉花或红薯、芝麻、绿豆、豌豆等。我家棉田在南地,因近河塘,呈不规则边型。
种棉颇为费时费力,除了要掰侧芽,还要防治棉铃虫,尤其夏秋交替之际,棉桃未熟,虫害尤甚,三天两头喷洒农药也除不尽。地头有一个盘子大小的水井,母亲背着药箱在田间打农药,我在井旁打水,一个小红塑料桶系上麻绳下到井里,麻绳是爷爷用秋天割的野麻搓成的,坚韧结实,一桶一桶提上来,倒进大铁皮桶里,水快打满时,母亲药箱里的农药也差不多打完了,就跑到井旁准备倒水兑药打第二箱。有时母亲打得慢,我将铁皮桶灌满后,便跑到离井不远的河塘边玩耍,有时摘几朵蒲公英,对着它们吹气,让它们的小伞四海八荒飞去。有时就在井旁坐着,或看书,或看鸟,或看蚂蚱蛐蛐在草丛里蹦来蹦去。
棉花盛开时,母亲在清晨采摘,因为霜寒露重,摘时不会掺杂碎叶子、碎花壳或干草之类的杂质。母亲常教育我们要干干净净做人,她摘棉花自然也要干干净净。采摘回来的棉花被母亲均匀地铺在平房顶上,在阳光下晾晒,喧腾起来的棉花好像一群落地的白鸟,做着欲飞的姿势,又似一朵朵白云,做着等风飘走的准备。我趁母亲不备趴在上面,那棉花带着一种清香,有岁月的甘甜,更有泥土的芬芳,我深吸不够,时觉如沐云端。
秋阳高照三五日,棉花便赶趟儿似的开得铺天盖地,母亲采摘不及,全家便齐上阵,白莹莹的盛开的棉花,有的四瓣,有的五瓣,鲜有六瓣的,张扬的举在顶端,内敛的隐在叶下。那时我觉得棉花真是田野里神奇的植物,它要开两次花,一次在初夏,花儿或粉或白,薄薄的花瓣似裙纱,在风里晃着;一次在深秋,花儿洁白如雪,是花更是果。采摘前,母亲给我穿上特制的围裙,围裙上缝有两个大袋子,采采白棉,不盈顷袋,我顺着田垄朝母亲跑去,把采下的棉花掏出放进母亲更大的袋子里,那小模样多神气,母亲的笑容有多甜,甜成了一朵盛开的棉花。
待到霜降,棉花要连棵从田地中收回。收回的棉花棵上还有许多未开的棉桃,所以把要它们晾晒开来,每到这时,院子围墙四周、小巷两边都被摆满了棉花,棉桃得阳光浇泼点燃,在枝干上炸出花朵,于是处处有花开,乡野清贫的生活之中瞬间生出难得的锦绣和诗意。棉花似乎没有摘尽的时候,即便到了冬季,母亲那干枯的棉花棵当柴烧,也能从中捋得几枚黑褐色的棉桃,剥开来,还是绵绵白絮,还有些棉桃硬得像颗顽石,或许还未来得及蓄起棉絮,便被岁月的刀剑风干,小小的、黑黑的,像是它留给岁月和我们最后的句点。
母亲每次留够了制作冬衣的棉花,便将多余的卖掉,所得钱财变成了我和弟弟的学费,所以母亲对棉花一直怀有感激之情。对于一个母亲而言,棉花既可以暖儿身,又可以供儿上学读书。在母亲看来,我和弟弟,其实是踩着一条铺满棉絮的路长大成人的,这是母亲对棉花最大的情结。可是对我而言,那棉花再好,也不及母爱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