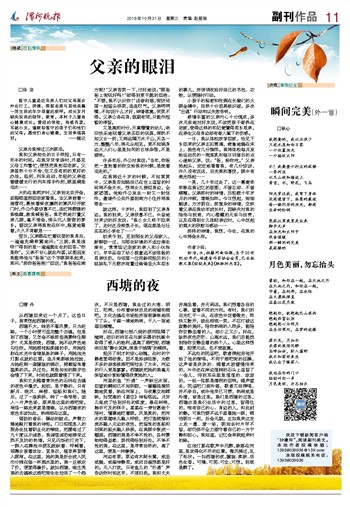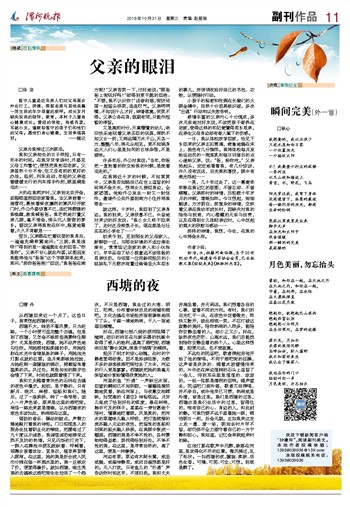□穆 丹
从西塘回来近一个月了,这些日子,我常想起西塘的夜。
西塘不大,倘若不看风景,只为赶路,一个小时便可逛完整个古镇。但是到了西塘,又怎会不被那些美景绊住脚步?尤其是夜晚,西塘,她不动声色地勾住你。用她柳枝般柔媚的手,用她投射在水光中含情脉脉的眸子,用她烛光灯影点就的红唇。连月亮都被她拉拢,为她赶制一袭朦胧的锦衣,裙裾摇曳着温柔的风。风过处,再急匆匆的脚步也会慢了下来,时间也就跟着慢了下来。
我和丈夫踏着青灰色的石砖在古镇的夜色中漫步。起初,是宁静的,只有新月、晚风、岸柳、摇船和我们。随后,过了一座拱桥,转了一条窄巷,误入一片声色场,原来是这里的酒吧街。难怪一路走来甚是清幽,以为西塘夜的底色本该如此,热闹却在这里。
强劲的音乐、躁动的鼓点,声嘶力竭地敲打着我的神经。门口招揽客人的服务生扯着职业化的喉咙,把腰弯过了九十度以示诚恳,我诚惶诚恐地接受这猝不及防的热情。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在舞池中胡乱跳跃着、呼喊着,领舞女孩着浓妆、紧身衣,搔首弄姿博人眼球。在这里,她的美是折合成人民币分摊在每一杯酒水里的。美一旦被定了价,便显得廉价。就如西塘,端庄秀美的古镇被这酒吧街生生拉低了一个档次,不只是西塘,我去过的大理、丽江、阳朔,分布着林林总总的商铺和酒吧。文化古镇在市场经济面前谦卑地低下了头,千篇一律地热闹,千人一面地眉目模糊。
好在,西塘七拐八绕的胡同阻隔了喧闹,老旧的砖瓦在与新乐器的抗衡中取得了感人的胜利。逃离了酒吧街,西塘依旧是“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模样。
经历了刚才的惊心动魄,此时的宁静愈显得珍贵。因不是旅游旺季,为数不多的游客被酒吧街拉去了大半,河边的行人更是寥寥。西塘就把她的美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懂得欣赏她的人。
河里的鱼“扑通”一声跃出水面,回望的瞬间已不知所踪,一圈圈涟漪狡黠地笑着,映在河面上,与夜幕交相辉映,如梵高的《星空》神秘悠远。月牙儿弯成了恰到好处的弧度,悬在树梢,触手可及的样子。星星在一旁甘愿做个陪衬,懂事地眨着眼。风是柔的,把河水的草腥味儿融入呼吸,把灯笼裙摆的流苏融入无边的夜色,把摇曳的客船和划桨的船夫融入桥拱,在我眼中嵌成一幅画。西塘的美是不争不抢的,各种景物相得益彰、烘托得恰到好处。不争不抢的美,在这里,是寻常自然的,离了这里,便是一种奢侈。
河边有草,草边有木制长凳,或坐或躺,或凝神静思,或闭目遐想都是好的。无人打扰,只有鱼儿的“扑通”声告诉你时间还早,不须归矣。我和丈夫并肩坐着,并无闲话。我们想着各自的心事,望着不同的方向。有时,我们的目光汇于一点,在夜色中泛着微光,很快又散开,彼此相视一笑,不忍打破这寂静的美好。陪你热闹的人很多,能陪你安静坐着的人,却少之又少。好在,纵然夜色茫茫、山高水远,我们总能找到陪你安静坐着的那个人。心里这样想着,即便无话,也不觉寂寞。
不远处的民谣吧,歌者弹起吉他开始了他的演唱。不同于酒吧街的狂躁,这声音是淡淡的、循着水波缓慢传来的,兴许还在岸边湿润的石头上逗留了一会儿,传到耳朵里是湿湿的、凉凉的,一丝一弦都是清冽的回响。循声望去,民谣吧门前冷落,歌者兀自弹唱,并不举目。或许他早已习惯,热闹或是冷清,皆是过客。我们是西塘的过客,西塘亦是我们生活中的过客,留得住的,唯有自己的心、身边的人,和此刻的静。可我仍要不远千里看她一眼,哪怕明日一别,后会无期。正如我来这世上走一遭、爱一场,明知去时片甲不留,却仍拼尽全力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宁静和初心。我知道,记忆会串联起来时的路。
红烛灯影在歌声中沉醉,跌落在河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红晕。微风拂过,乱了形状。一如西塘的夜,朦胧、柔软、活色生香。可嗅、可观、可念、可想。到底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