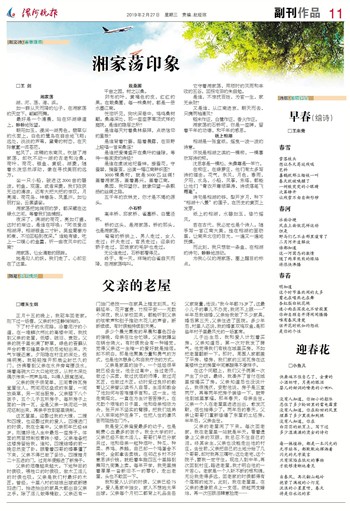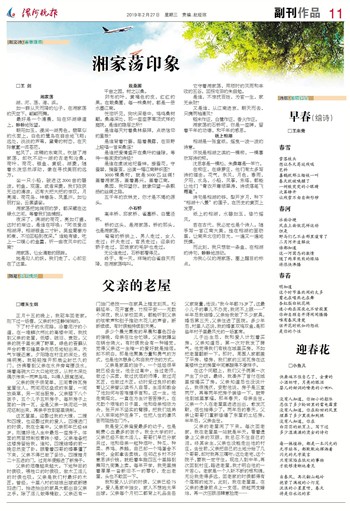□暖玉生烟
正月十五的晚上,我驱车回老家。刚下过一场雪,父亲的村庄静悄悄的。
下了村子的水泥路,沿着泥泞的小道,在一堆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我找到父亲的老屋,低矮、破旧、衰败。父亲的院子里长满了野草,绿色的苔藓从井台的青石缝里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天气乍暖还寒,夕阳隐在村庄的深处,极端明亮。我轻轻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门,仿佛看到父亲在水井旁弯腰汲水,端着海碗大口大口地吃饭。从树木深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叫得人眼窝湿润。
父亲的院子很简单,三间青砖瓦房堂屋住人,两间泥坯垒成的东屋,一间放柴草,另一间当厨房。父亲膝下八个孩子,五个儿子五所房子,每所房子上面的一砖一瓦,全是父亲一块泥坯一块泥坯制出来,再亲手放到窑里烧制。
这瓦屋里,迎娶过我的大嫂、二嫂和四嫂,也迎娶过我的爱人。四嫂进门的时候,我在念高中。父亲那年已经68岁,刚建好他人生中最后一座房子,体面的两层预制板青砖小楼,父亲准备把这楼房留给我。谁知,四嫂结婚的前一晚忽然变了卦。眼看着四哥的婚事僵了下来,父亲不得已做了妥协。四嫂腊月二十五进的门,过完年便搬进了新房子。
父亲的烟瘾越来越大。下地种田的时候吸,喂牲口的时候吸,做木工活儿的时候也吸。父亲是我们村最好的木匠。曾经,十里八村的姑娘出嫁或新媳妇进门,抬进抬出的家具大都出自父亲之手。除了活儿做得精致,父亲还有一门独门绝技——在家具上描龙刻凤,松鹤延年、花开富贵、竹报平安……无数个深夜,我从学校回来,都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和刨子推动木花儿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时候能持续到天亮。
多少个晨光熹微的早晨和暮色四合的傍晚,母亲在灶台忙碌,父亲就蹲坐在锅台烧火。有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觉得父亲这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抽烟。却不明白,那是他聚集力量和勇气的方式,也是他休憩身心和自我疗伤的方式。
父亲是家里的独子,一个姐姐很早就已经去世。他念过高中,当过老师,做过小买卖,做过炕烟的师傅,做过泥瓦匠,也做过木匠。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让父亲曾以读书人自居,生活却教会了他如何与苦难握手言和。这一生,他走南闯北,一直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在无数个艰难的日子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张开并不坚实的臂膀,把我们姐弟八人牢牢地护在身下,也把人世的凄风苦雨阻挡在门外。
我是受父亲偏爱最多的幼子,也是耗费心血最多的孩子。我念大学的时,父亲已经不做木活儿。哥哥们早已分家另过,他和母亲一起种烟叶、种瓜、种菜、养鸡、养鹅,自己却一个鸡蛋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钱。在邻近乡村不好意思讲价钱,就赶着车跑四五十里路到舞阳九街集上卖。每年开学,我兜里揣着厚厚一沓新旧不一的零钞,走出老屋,头也不敢回一下。
我和爱人认识的时候,父亲已经75岁。爱人是家中独女,家人不想她太早出嫁。父亲每个月初二都背上礼品去岳父家商量,他说:“我今年都75岁了,这最小儿子的事儿不办完,我闭不上眼……”半年后我结婚,父亲给我做了不少家具,婚后第三天,父亲住进了医院。多少年后,村里人还说,我的婚宴双鸡双鱼,是那些年村子里最风光的一场宴席。
儿子出生后,我和爱人计划着买房。父亲知道后,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他觉得我们有钱在城里买房,不如把老屋翻新一下。那时,周围人家都盖了平房、楼房,我们家的三间瓦房在这高楼林立的房屋中间寒酸得不像样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父子俩第一次产生了分歧。最终,我凑齐了首付在城里按揭买了房。父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我很愧疚,安慰他说,房子是三室两厅,再等两年把房子装修一下,就带他到城里享福。那年春天,母亲去世。父亲一个人在老屋里进进出出,愈发沉默,烟也抽得少了。两年后的春天,父亲让哥哥们重新修缮了东屋的土坯房。半年后,父亲去世。
父亲的老屋闲了下来。每次回老家,我在老屋里一站就是半天。看着遗像上父亲的双眼,我总忍不住自己的泪。终其余生,父亲也没能走出他的村庄。去世前,父亲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几个哥哥,却对我再三嘱咐:这处老宅,这个院子,要我一定守住。现在人到中年,再次回到村庄,踏进老屋,我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老家是一个人斩不断的根和魂,无论我走得多远,回老家的时候都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此刻,我在老屋里,在父亲的遗像前点上一支烟,燃起两支蜡烛,再一次任眼泪肆意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