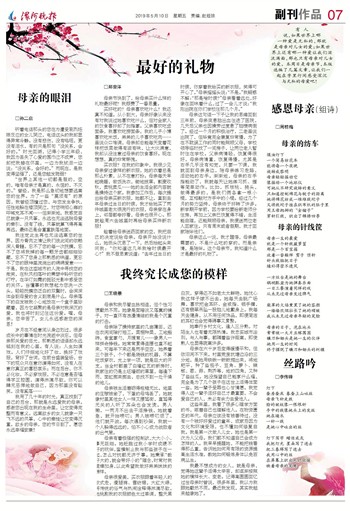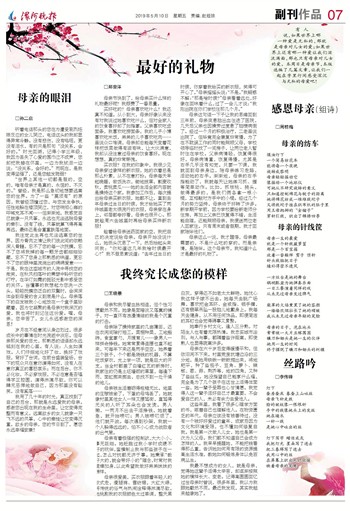□王晓景
母亲和我尽管血脉相连,但个性习惯截然不同。她像是面暗淡又落寞的镜子,对一直怀有浪漫情结的我是个沉重的打击。
母亲除了操持家里的几亩薄田,还在农闲间隙打短工。菜棚种菜,工地搬砖,食堂掌勺,月嫂育儿……像男人一样拼命挣钱。她常常累得连腰也直不起来,可每年下来还是两手空空。她养着三个孩子,个个都是烧钱的机器,不算吃饭穿衣,光上学一项,就是巨大的开支。当全村都盖了白墙红瓦的新房时,我家住的仍是土坯墙砌的草屋,每逢下雨,面缸挪来挪去,总找不到一处干燥的地儿。
母亲被生活磨砺得粗糙无比。地里的庄稼被偷了,下蛋的母鸡丢了,她就像村里其他女人一样叉腰骂街,直骂得无关的人听了耳朵也会发烫。男人懒,一两月不出去干活挣钱,她就着急,就开始唠叨;男人被唠叨烦了,他们就开战。每次遇到吵架,我就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怕不小心成为战败者的出气筒。
母亲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大大小小,事无巨细。她赶跑过我小学时成绩不好的玩伴,蛮横制止我与那些孩子在一起,怎么对抗都无济于事。她秉承“教好大的,就会带好小的”理念,时常对我棍棒加身,以此希望我做好弟弟妹妹的榜样。
母亲很爱美,买衣服跟着年轻人的款式走,瘦腿裤、雪纺裙,大红大绿,将传统的俗气与热闹诠释得淋漓尽致。她挑剔我的衣服颜色太过单调,整天黑白灰,穿得还不如老太太鲜艳,她忧心我这样子嫁不出去。她每天去跳广场舞,喜欢把金耳环、金戒指、银手镯,还有翡翠吊坠一股脑儿地戴身上。我每天去健身,从不用任何饰品,即便简洁的耳钉也会觉得碍事又累赘。
她奉行乡村文化,逢人三分熟,对陌生人也有着无限热情。我忠实城市法则,与人与事,都隔着些许距离,即使熟人也显得疏离许多。
母亲在六十岁后变得缓慢平和,但依旧闲不下来。村里荒废坑塘边沿的三分地,是她用铁锹一锨锨掘出来,将地耙平,种了些茄子、豆角、萝卜、辣椒、葱、蒜、荆芥等,地的四角,又种了些丝瓜。她没指望自己能享什么福,完全是为了几个孩子在这世上活得体面一些,她一辈子受罪也心甘情愿。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活好自己才最重要,不会爱自己的人,未必有余力去爱他人。
这些年里,我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琢磨自己也理解他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应该没有被善待过,没有一个被好好爱过的童年,成家后因为文化和环境受限,也不懂如何修复自我。我是第一次做人儿女,她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我早早提醒她,不能把钱看得那么重,告诉她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提高生活水准,教她如何锻炼身体以免百病丛生。
我最不想成为的女人,就是母亲,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辛苦,却逐渐按照她的模样长大、变老。记得高圆圆回忆过世母亲时曾说,很多年里,我以为我跟她截然不同。最近我发现,其实我越来越像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