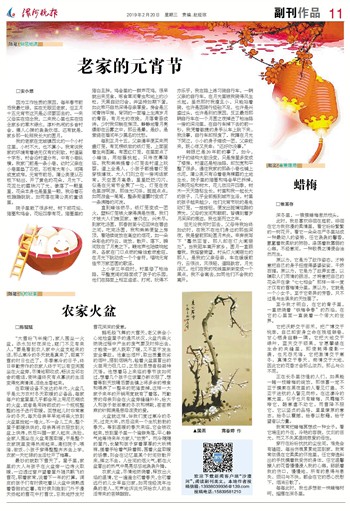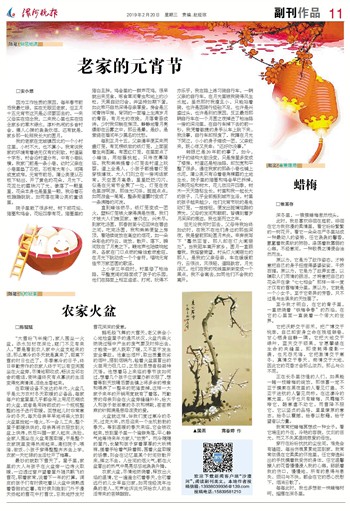□安小悠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每年春节前后我最忙碌,实在无暇回老家,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是必须要回去的,一来父母实在惦念我,二来我心里也实在惦念家乡的草木绿水,淳朴热闹的乡音村舍,摄人心脾的袅袅炊烟,还有就是,家乡那一轮照我长大的圆月。
我的老家在龙城镇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小村不大,也不算小。我常说我家的环境有着绝无仅有的别致,村道呈十字形,村舍沿村道分布,中有小巷纵横。我家门前是一条小巷,幼时父亲在小巷里垫了石板,石板有大有小,间隔或宽或窄。元宵节前后,蒲公英便从石板下钻出,开了黄色的花朵,月光下,花蕊处的露珠闪了光,像落了一颗星星,花朵本身也是星星一颗,我沿着石板蹦蹦跳跳,如同落在蒲公英的童话里。
院子里栽了很多树,树下砌花坛、猪圈和鸡舍,花坛四季有花,猪圈里的猪白且胖,鸡舍里的一群芦花鸡,很早就出来觅食,啄食草间青虫和地上的沙粒,天黑自动归舍,并坚持如期下蛋,如此乖巧自然深得母亲厚爱。房舍是三间青砖平房,背阴的一面墙上生满岁月的青苔,有月光的夜晚,月落青苔成诗。少时我仰躺在房顶,静静地看月亮缥缈在云雾之中,那云是晕,是纱,是萦绕在眉间年少莫名的忧愁。
每到正月十五,父亲清早便买来两盏灯笼,有瓦楞纸做的纸灯笼,上面画着生肖图案,有圆红灯笼,在里面点了小蜡烛,用细藤挑起,只待夜幕降临,我和弟弟提着小灯笼去村道上玩耍,道上全是人,小孩子都提着灯笼穿梭嬉戏,大人们则立在一旁闲话家常。天空圆月高悬,星星眨眨闪闪,似是在元宵节全聚了一处,灯笼在夜色里游啊游,那烛光闪烁,斑斑点点,如同游鱼一尾尾,整条街道霎时变成了一条沸腾的河流。
直到蜡烛燃尽,纸灯笼变成一团火,塑料灯笼被火燎得满是伤痕,我们才被大人们拽回家,意仍在,兴未尽。到家吃汤圆,那香甜至今还回味在唇齿之间。吃完汤圆,我和弟弟便登上房顶,看陆续绽放在高空的烟花,如一朵朵彩色的行云,绽放、散开、落下,瞬间败在了月亮之下。鞭炮声也陆续响起来,各家在门口点燃的蜡烛愈燃愈旺,在月光下跳动成一个个音符,唱响元宵佳节万家团圆的歌谣。
上小学三年级时,村里修了柏油路,平整宽阔的路面成了孩子的乐园,他们在路面上相互追逐、打闹,玩得不亦乐乎,我在路上练习骑自行车,一辆父亲的自行车,在月光里被我骑得风生水起。虽然那时我瘦且小,只能站着骑,也许是因骑行经验不足,也许是兴盛过头,也许是别的原因,反正最后那辆自行车在一个月圆之夜掉进了柏油路一旁的深沟里,在自行车掉下去的前一秒,我凭着敏捷的身手从车上跳下来,我没事,自行车却报废了,我蹲在月光下哭泣,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父亲赶来,既心疼又庆幸:“还好你没事。”
转眼已是20年前的事了,如今,村子的结构大致没变,只是房屋多变成了楼房,村道还是柏油路,却加宽和平整了很多,通往我家的那条小巷也铺上水泥,蒲公英只有沿着巷角裸露的土地生长,院子里的猪圈和鸡舍早已拆掉,只剩花坛和树木,花儿依旧开四季,树木一天天隐秘生长,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几乎全部搬到城市生活,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他们元宵节玩的是电动灯笼,一按按钮,便发出斑斓炫酷的声光,父母的发间和额前,皆镌刻着岁月深深的痕迹,我也至而立之年。
但无论我何时回去,父母待我始终如幼时,在我不在他们身边的那些深夜,我是窗前那轮圆月未央。辛弃疾写下“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驱车离开家乡,圆月一直跟着我,我摇窗倚望,村头灯火阑珊处的那人,是我的父亲母亲,车在缓缓前行,云很淡,风很轻,道路跌宕,月光浮沉,他们在我的视线里渐渐变成一个黑点,我不舍离去,如同他们不舍我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