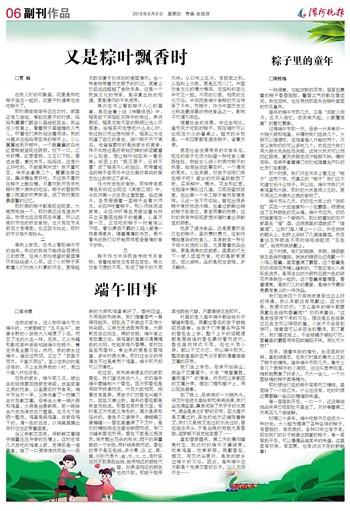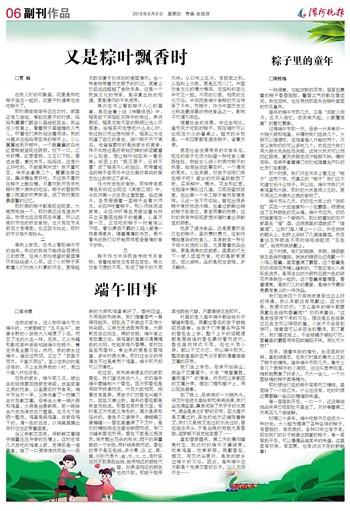□安小悠
在我的家乡,没人称呼端午节为端午的,大家都喊它“五月当午”,就像乡野的小孩被大人喊惯了小名,而忘了他的大名一样。后来,又从书籍和影视剧中渐渐知晓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主要习俗。然而,我的家乡过端午,偏没这两项,正应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至少在我幼时是没有的,不止生我养我的小村,周边十里八村也没有。
在我的家乡,端午前几日,嫁出去的姑娘要回娘家走亲戚,送些变蛋之类的吃食,以备麦收时节食用。端午节当天一早,父亲先拿了一把镰刀去村后割艾蒿。母亲生火煮一锅大蒜和鸡蛋,大蒜是当季新蒜,前一晚除去外皮洗净放在竹筐里,在月光下晾晒一整夜。鸡蛋是柴鸡蛋,自家母鸡下的,清一色的白皮,从鸡窝里摸出来时往往还带着温度。
当父亲割艾回来,将新鲜艾蒿随手搁置在压井旁的石槽上,这时总有几只贪吃的鸡凑上前,觉得那是一堆美食,尝了一口便悻悻然而去……母亲的大蒜和鸡蛋煮好了,香味四溢,不用唤我和弟弟,我们循着香气一骨碌爬起床,胡乱洗了手就迫不及待大快朵颐。父亲也走进厨房同食,大蒜熟后洁白如玉,绵软甘甜,端午食之有败毒之说。柴鸡蛋的蛋黄似清晨橘色的太阳,吃起来格外香糯。有时加些盐和香料,煮出来的便是五香鸡蛋,多半时候水煮。那时过生日的待遇也不过是煮两个鸡蛋,端午那天却可以尽情吃。
吃过饭,我和弟弟便去奶奶家取香包,我们堂兄妹共六人,奶奶每年端午要缝制六个香包。因为那香包是用碎布拼凑而成,外观大致相同,细看总有差异。男孩子们对香包兴趣不大,姐姐又谦让我,每年的香包都是我首先挑选。那香包有时是元宝,有时是正方形或三角形的,偶尔是奇形怪状的,像兔子又像猴子,像蝴蝶又像蝙蝠……香包里塞满了干艾叶,是奶奶精挑细选在窗台晾晒而成,专门为缝制香包而用。香包下面是三根流苏,用布剪出花朵的形状,晒干的蒜薹裁成一寸长短,用针线串联而成。香包的带子是五色线,多为青、白、红、黑、黄,分别代表木、金、水、火、土,有时实在找不到某色丝线,就用相近的颜色代替,如果连相近的颜色也找不到,那就干脆用其他颜色代替,只要凑够五色即可。
村里的老人每年端午都会给孙子辈缝制香包,佩戴过香包的孩子就能驱邪避害。当孩子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香包去上学,整个上午的话题便都是围绕谁的香包最好看而进行。香包虽然样式不同,但也大同小异,都以干艾为芯,所以端午那天,整间教室里的空气似乎都弥漫着缕缕艾蒿的芬芳。
我们去上学后,母亲开始除尘,燃些干艾熏屋子,大有“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的情境。然后把父亲割回的艾蒿分束,插在门楣和窗户上,用以驱虫避害。
到了晚上,母亲烧好一大锅热水,将艾叶泡进水里给我和弟弟洗澡,我们坐在澡盆里,鼻息间除了热乎乎的水蒸气,便全是身处旷野的芬芳。因为屋子是艾熏过的,其他的地方还铺陈着鲜艾,我们又是被艾泡过的水洗过的,香包挂在床头,于是当晚的觉就尤其香甜,连梦都不自觉地变香了……
直到香梦醒来,第二天的晨阳擦亮村庄,我幼时的端午才算结束。吃煮鸡蛋、吃煮新蒜,佩戴香包、插艾、用艾沐浴更衣,是我的家乡过端午的习俗。因此,每年端午这天都是个充满艾香的日子,让人无限怀念……